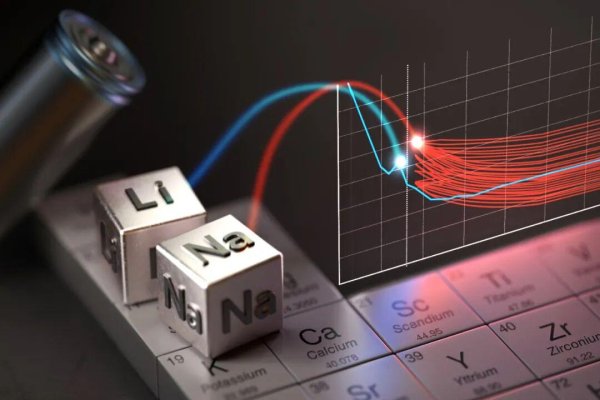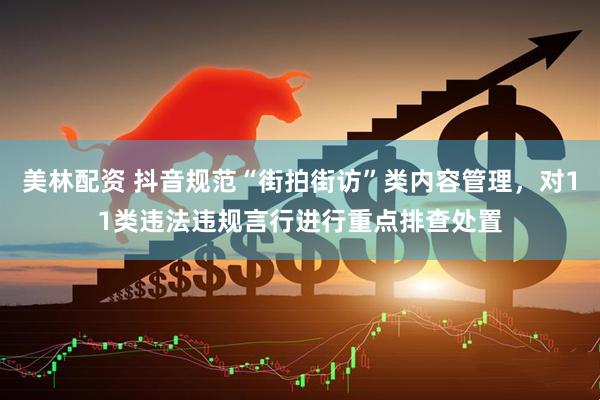连载速牛配资
作家薛喜君的长篇小说《沾别拉》近期在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,作品以沾河林业局“守塔人”为原型,生动再现了四代森工人守护山林、转型发展的奋斗历程,是生态文化与文学创作的有益尝试。在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提出20周年之际,我们连载此小说,以飨读者~
作者简介:薛喜君,女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黑龙江省作协签约作家。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,以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见长,出版发行《二月雪》《白月光》等,作品多次获奖。
二十八
高科举家是后搬到龙镇的,他祖上是安县的坐地户,安县距离龙镇有百十多里地。
高家世代靠开中医馆为生。中药馆在高科举的爷爷手里败落。当时时局动荡,他家还遭遇了乡野恶人的讹诈,中医馆只得以出兑的方式抵出去。名义上是出兑,可人家没给一文钱。就连祖传的秘方都被搜刮出去了,高科举的父亲亲眼看见了父亲含冤而死的过程。高科举的爷爷死后,父亲就担起破落家族十几口人的生活。起初,他想重振中医馆。但高氏中医馆就像一只飞鸟,悄无声息地飞走时,连一片羽毛都没留下。为养活一家人,父亲只能背一杆猎枪,干了上山打猎的行当。
展开剩余94%高家虽然没能找回昔日的风光,但总算从差点儿流落街头乞讨的悲惨境遇里一步步走出来。
高科举十四五岁就跟着父亲在山里与猎物周旋,顺带着辨认草药。他从小就在小兴安岭的朔风里淬炼,骨子里的豪爽也是在山峦上练就的。父亲告诉高科举:“山脊是猎人的路,好猎人就要走遍脚下的路。一个好猎人就该对动物、植物怀有感恩和敬畏之心。”高科举牢记父亲的话,从小就对乌斯孟、北沾河、南沾河、老爷岭、雀儿岭十分熟悉,就像山里的一只猴子,不仅熟悉动物的习性,对山上的植物、上山的路也都了如指掌。
“高家几代传下来的中医馆,没能传承下来,你爷到死都没闭上眼睛。”父亲又看了高科举一眼,“你爷没能把中医馆振兴起来,觉得对不住先人,对不住我。我没能让高氏中医馆重整旗鼓,对不住先人,也对不起你。早先,我心里对你还寄托一线希望,想不到你的心思却不在这儿。看来咱们高氏中医馆真的彻底死了。”父亲哀叹一声,一直惦记着把高氏中医馆的牌
匾再挂出来的父亲,终于认清了,高氏中医馆大势已去。别说他不能重振,就是他的儿孙,也无能为力。
或许,父亲还预料到自己的气数到了,也预见到了林业的未来。于是,父亲带着全家搬到龙镇。搬到龙镇的第二年,父亲就病倒在炕上了。躺在炕上奄奄一息的父亲,把高科举叫到面前:“儿啊,放下猎枪,去做林工吧,毕竟那才是正经行当。记住,只要放下枪,就不要再去打动物,一只飞鸟都不能打。”父亲说得十分吃力,但语气坚定,“也不要再碰药材了,中医馆的念想,就在你这儿断了吧。”
父亲不久就离开了人世。
高科举依照父亲的遗愿,进了山河林业局,成了林业工人。
起初,他被分配到集材队,他自己也想去集材队。他说跟着父亲在山里转了数年,见识过牛马套把原条从山上拉到江边,再堆起高高的木楞。等到冰雪融化,桃花水从山上下来时,再把堆积如山的木头,一根一根推到水里,利用湍急的水势,把木头送到山下的河场。下游的工人再把木头打捞上岸,归成楞垛。但水运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,相对而言,困难多,工序也多。单往中楞运输这一环节,就需要很有经验的老把式。弯把锯把树伐倒后,打丫子,造件子,而后再用人工或者畜力,把原木拖到事先浇好的冰沟、冰道里,出溜到山下,再用牛马套子倒到中楞,这一环节只能在寒冷的冬季进行。再就是归楞,归楞的好处是,除了节省占地面积,还易于入水。工人们要用搬钩和滚扛依次把原木滚入河中,林业人都称之为件子。楞上的件子也是顺势依次而下,省了力气和时间。原条滚入水后,能自上而下地顺势漂流。
高科举还看见过“放排”和“赶羊”。放排和赶羊的场面,十分壮观。顺畅时,汹涌的河水咆哮着将数千米木材流送到目的地。遇到水势不顺的时候,死人伤人的事儿也常见。放排工被水流冲下去,再不见踪影的事故,时有发生。他小时候看放排和赶羊,只是觉得好玩。年岁再大一些,他对此就有了浓厚的兴趣。
山河林业局,最初也想学习其他兄弟局的水运集材方法和经验,就成立了集材流送队。陈二就是山河林业局最早的流送工。早年,他曾经为木帮、为日本人放过排。当年,他被特招进山河林业局,就因为他是成手的流送工。
看过陈二放排的人都夸赞他,说他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人,是放排的好把式。
正是这次流放,致使山河林业局彻底放弃了水运。
立春的节气,总是能让人生发出希望。
立春这天,龙镇家家户户都烙春饼、啃青萝卜。风,如同春天的序曲。尽管春风来时的样子,有失体统,也有些丑陋,但它不嘶叫,也不能撼动坚硬的大地。从这天开始,人们就走出了冬天的寂寥。大沾河的冰层也开始松动,冰层下的水暗流涌动。住在大沾河两岸的人,不会错过跑冰排时的壮观场面。挣脱的冰排,生命进入倒计时,也要奋力一搏。冰排用沉闷撞击的响声和溅起的水柱告诉人们,即便是粉身碎骨,也要死得轰轰烈烈。四月末,大大小小的冰排,宛若白云,向下游轰隆作响地冲撞。待到冰排融化殆尽后,原木流送的时机就来了。
已经进了林业局的高科举,跑去看流送时的壮观场面。就是这次,他见识了陈二放排的技艺。
开始,水运很顺利,一根根原条顺水而下。山河林业局人大多是第一次看到水运。看到壮观的河面,人们都为原条在水里的畅游而欣喜若狂。但在下游的一个水湾处,几根捣蛋的原条挡住了其他顺水而下的原条的去路。眨眼工夫,数百米的原条就碰撞着堆积起来。有的不堪重击,突然腾空蹿起数米高,“咔嚓”一声,一根原条拦腰折断。溅起的水花和木渣儿,打在人们的身上,人群水浪一样地往后退。随后,刚才还顺溜的原条,如同冰凌似的拱了起来,而且越拱越高,瞬间就堵塞了河道。原条越聚越多,在水流的冲击下,拱起来的原条宛若一座山丘。顷刻间,水面像患了肠梗阻,河水无声地漫延到岸上。
吓得人们“哇”一声,朝后退去——眼看着一场灾祸就要发生。只听一声长长的呼哨,手持长竹竿的陈二,跳到一根原条上。他手里的竹竿瞬间化作撑船的桨,在激流中左挑一下,右撅一下,三下五除二就理顺了七零八散冲撞过来的原条。他像一只灵活的猴子,从这根原条跳到另一根原条上,躲过迎头撞击过来的树木后,又跳到自动拱起的原条堆上,手里的竹竿再次上下翻飞。拥堵的一垛原条在他的竹竿下,宛若一只只羊,被他归拢到水流湍急的河道中。一根根原条顺着水流漂走了。
大水挟着原条又冲了过来。陈二看准机会,顺势骑上一根原条,顺水漂流而下。站在岸上的人们都惊讶地张大嘴巴,眼睁睁地看着陈二变成一个小黑点,顺水漂走了。
两天后,陈二才得以返还。他一脚刚迈进外屋,刚剪断脐带的儿子的哭声传了出来。陈二惊得站住了速牛配资,没一会儿,呜呜的哭声从外屋传进来。陈二的哭声像屋檐下的风,呜呜声中还带着呼哨。陈二妈侧耳听出是儿子的哭声,说让他哭,憋在肚子里的东西,哭出来才不会生病。
陈二哭够了。按他妈说的,把肚子里的东西都哭了出来。他突然觉得饿,扯着嗓子喊:“妈,给我拿几块饼子。”
陈二妈掀开碗架上的布帘,从盆里掐出两块饼子递给他:“先给你儿子起了名儿再吃。”陈二想了一下,“叫水生吧。我刚从水里逃生回来。”
陈二从他妈手里接过饼子,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
从那以后,山河林业局也意识到,兄弟局的经验,在山河林业局不太好用。山河林业局施业辖区没有很适合这种经验的地理环境,还受水位的制约和气温的影响。再者,水上流送,风险太大,损耗也大,有太多弊端,危机重重。
因此,水运集材在山河林业局被彻底取缔。
二十九
山河林业局成立之初,木材生产基本是沿袭伪满时期的作业方式。九月,林区人就开始秋收。十月,田地里的庄稼收完了,人们就赶着牛马套子进山伐木,利用冰雪的滑力和牛马套子,把伐下来的树木运到山下。
林业人称之为“冬采夏留,一股肠子拿木头”。采伐和集运,完全是靠人力。即便有牛马,多数时候,还得靠人。虽然费时费力,但比起水运,还是好很多。
一到十月,小兴安岭地区就普降大雪,封冻的大地宛若僵死的虫子,生命气息不见了踪影。尽管大雪封山,但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大山上,人欢马叫。高科举所在的集材队,也隶属于木沟壑林场。当时集材大多是人拉肩扛,先是用掐钩将原木集中成小山楞,林业人管这叫吊铆,然后再用牛马倒挂子集材,运到中间楞场。归楞时,完全使用肩扛,把门,掐钩。小木头四个人抬,大木头八个人抬,一副杠,分拉头杠,二档子还有耍龙的。集材也如跑冰排般热闹壮观,归楞场人喊马叫。
集材的牲畜,都是林业局从当地农户手里租来的。
脑瓜活泛的林工家属,看准这个来钱的道,也养起了牛马,每年冬天集材时就租给林场,一冬天下来,省了饲料不说,还能挣几个钱贴补家用。
高科举可谓老林工了,资格比杨石山老,对集材十分在行。为了贴补家用,挣两个零花钱,张桂兰也养了一匹马。一到冬天,高科举就牵着马匹上山。牛马也偷奸耍滑,人若是不看着,陡峭的路,滑得像镜面的冰雪路,牲口也打怵。它们站在原地不肯挪步,人要是不用鞭子抽它,它才不会主动去冒风险。
牲畜集材,主要的劳力还是人。集材光靠牛马,不出活儿不说,也远远跟不上采伐的进度,只能人上。因此,集材工们的肩膀,个个长着“血蘑菇”。肩膀的皮薄,皮下就是骨头。抬一天木头,重力透过羊皮坎肩,透过棉袄,皮就磨破了。没了皮,就只能磨骨头了。林工们也称集材队为磨骨头队,还说他们是一支很专业的磨骨头队。
集材工抬木头的气势震撼。磨骨头十分讲究配合。人们不但要互相了解,还要彼此信任。当一根木头被抬起来时,号子就响起来,步伐整齐。看似悠然自得,看似无比轻松,其实每个人都不得有半点儿疏忽。高科举一定是喊号子的那个人,他的嗓门大,还透亮,喊号子的节奏也好:“哈腰挂嗨——吆嗨嗨——”掐钩就被牢牢嵌入原木里。“撑起腰啊嗨——哎嗨呦——”木头就在悠长粗犷的吼声里起来了。“哥儿几个呀,朝前走啊——”工友们就都抬头挺胸抓紧杠头,脚下的步伐也要绝对齐整,一晃一晃地朝楞垛走去。
人与原木的重量,压得跳板颤巍巍,嘎吱作响。但他们脚下稳,不能有一个人散脚。
姜占林在集材队时,和高科举配合得非常默契。遇上“水罐子”,长度在八米多的木头,就重达几千斤了。四人肯定不行,六人也有些费劲,基本上都是八个人抬。高科举一定是头杠,姜占林就压后阵。姜占林后来调离集材队,到领导岗位任职,他们才分开。
高科举担任队长后,依旧延续着姜占林的管理模式。“要想把集材干好,光有力气不行,还要嘴勤、脚稳、手快、眼尖,好集材工,不是一年半载就能练出来的。”他心思细腻,对集材工十分爱护。集材工每天从天刚蒙蒙亮开始劳作,到天一擦黑才下工。集材队的集材工,一天下来,肩膀的皮肉开裂,两天就露出骨头。沾着血水继续压,继续扛,继续磨,一块硬硬的鹅蛋大小的肉疙瘩就鼓了起来,这就是“血蘑菇”。
“血蘑菇”是林业工人的标志。集材工也都为自己肩膀上的“血蘑菇”
而自豪。这让高科举很难过。每年冬季除了动员林业职工,还要动员大量农民带着牲畜上山突击运材,但这样也不能保证完成生产任务。一个采伐季下来,弄得人困马乏不说,还影响生产。这种情况下,如何才能大干、实干、巧干——突然,“巧干”两个字在他脑子里闪电似的震得他一激灵。是啊,为什么不能巧干?他的脑子飞快地转,他迅速走出家门,把集材队的骨干召集起来。于是,一场林业生产技术改革,在高科举的带领下,悄然地开始了。工作之余,骨干们没事儿就凑到一起研究。高科举经常把工友带到家里喝酒。林工们对酒有讲究,但对菜不太讲究。木耳炒白菜片、土豆丝,要是再抠个咸鸭蛋,炒一盘花生米,他们就能喝得热火朝天。酒,一定是新鄂乡鄂伦春人的纯粮小烧。
喝酒时,高科举又讲起陈二的故事。他说:“今天的生产,和过去完全不同,那时候的集材方式能满足那时候的需要。那时候需要像陈二这样的流送工和我们这样的集材工。可现在不同了,咱们若是还停留在那个时候,咱们的儿孙也和咱们一样。那样的话,咱们可真是献了自己,又献了儿孙。所以啊,咱们也不能只顾着大干、实干,还要在巧干上用心思。”
高科举的话让大家兴奋起来。“对,要巧干。再不巧干,别说生产搞不好,咱们的身子骨也累垮了。”借着酒劲,工友们七嘴八舌,纷纷说出自己的想法。他们先是在纸上画,再利用小木块模拟滑道,一遍又一遍计算,一遍又一遍模拟。高科举如醉如痴地深陷其中。吃饭,他用饼子搭;抽烟,他用火柴盒一遍遍模拟,一次次推倒……他还把姜占林找来喝酒,让他帮忙出主意。
姜占林十分感动,除了提建议和想法,还从家里拿酒拿菜。
高科举把大家的想法归纳起来,在纸上写写画画。他骄傲地对张桂兰说:“这字不白认,书也不白读。”小时候,爷爷就教他认字,爹后来虽然跑山,但也能看大书。他也跟着爹读,看到不认识的字,就问爹。爹看的都是线装书,还是繁体字。所以,无论是繁体字,还是简体字,都难不住高科举……经过无数次试验,最后,高科举觉得用冰雪槽道的方法更可行,更适用老爷岭、
雀儿岭等施业区的采伐和集材。采伐季开始之前,集材队就准备好了。冬季采伐的号子一响,集材队就把焊着轱辘的铁炉子带到山上。上山后,依据施业区周边的地理特点,在炉膛里架上劈柴,两个人一边一个拽着铁炉子,顺着山坡往下滑动。铁炉子所到之处,雪开始融化,最初的槽道雏形就出来了。铁炉子来回走两三趟,一条槽道就开了出来。打丫子、造件子后的原条,顺着开出来冰槽道的坡度速牛配资,自动归楞。
高科举又根据自然规律,以及施业区的环境,总结出“有坡自动化,无坡一条龙”的网道化、逆坡化集材作业方式。这种集材方式先是在高科举这个队试行,在姜占林的关注和倡导下,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就在林业局全面推广。于是,各个施业区的冰雪槽道网,遍布山岭。伐下来的木材,驯服地顺着槽道剑似的从山上自动飞奔下来,并灵巧地爬上楞垛,自动垛好。
“老天爷都输给了我们。”高科举自豪地说,“工友们加油干吧。”
当年,高科举被评为林业局革新能手。除了一个镶框的奖状,他还得了一个铁皮暖瓶。
三十
采伐季一结束,高科举牵着自家的马下山,张桂兰看到瘦得骨头都支棱出来的马,呜呜地哭开了。她埋怨男人没照顾好马匹,光顾着喝酒,把马累得都散架子了。高科举苦笑,说:“你看看我,我比马还瘦,我的骨架子要不是有筋连着,早就散了。你不为我哭,却为一匹马哭?这是何故?你不心疼男人,倒心疼起牲口来。”高科举看着她,“找个主,把马卖了吧,再养马就赔钱了,以后集材用不着马了。”
张桂兰“扑哧”笑了,抹去脸上的泪水,想想也是,马匹咋还比男人金贵?她自知不占理,就悄悄坐在灶台前烧火做饭。此时,为男人做一顿可口的饭菜,才是她该做的。
吃饱喝足,就该睡觉了。张桂兰撵儿子:“去,去炕梢儿睡,今晚的火烧得多。小孩子睡太热的炕上火,鼻子容易出血。”高守权就骨碌到炕梢儿。高守权正是贪吃贪睡的年龄,可这晚,他却翻来覆去不睡,眼珠叽里咕噜地瞄着炕头儿。因为家里多了一个人,一冬天没在家的爸回来了,他也想和爸亲近,可妈让他睡炕梢儿。
高科举洗头刮胡子,又把衣裳泡到洗衣盆里。儿子的目光追随着父亲的身影,他还不时地发出笑声。脑袋收拾完了,高科举又烫脚。他烫脚可真慢啊,还不时往盆里“哗哗”地加热水。高守权都看痴了。高科举终于从盆里抽出双脚,但并不急于擦干脚上的水,而是任凭脚上的水滴答滴答地淌回盆里。他拿过擦脚抹布,终于上炕了。躺在炕头儿的张桂兰,脸冲墙装睡,对他不理不睬。他碍于孩子,不敢有啥大动作,只能手从被窝下探过去,轻轻地揪一把女人腰上的肉。她腰上除了松垮的皮,没有肉。张桂兰没阻拦,他的手继续往上游走。这下,张桂兰不干了,掐他一把,还
把他的手推出来。高科举只好把手缩回来,他听到张桂兰没说出来的话:儿子还没睡。
一冬天都没睡到热乎炕了,一钻进热乎乎的被窝,高科举全身的关节都舒展开了,从骨头缝儿往外冒凉气,身子一热乎,困意不可遏制地来了。他在黑暗中努力地想睁着眼睛,先是盯着在窗口探头探脑的一钩弯月,想心事。想着想着,他睡着了。张桂兰听到身边男人的鼾声,气得一耸身子,又转了过去。
高科举一觉睡到大天亮。早上,张桂兰粗声大气地叫高科举:“快起来吃饭,睡得像头猪,太阳都上天了。”高科举“咔哧咔哧”地挠头皮,“昨晚我咋就睡着了?儿子呢,上学去了?”
“你咋能睡不着。你心里除了山,就是木头。你不想别人,就不耽误睡觉。”张桂兰说完一扭身去了外屋。
高科举看看炕梢儿,看看屋里,又看一眼院子,儿子上学去了。他起身去了外屋,把张桂兰从锅灶前拎到里屋的炕沿上。“一天老怄气,动不动就怄气。你是气蛤蟆吗?我叫你怄气,叫你怄气……”开始,她还手抓脚蹬,当男人粗重的喘息喷到她脸上,她的耳朵和脖子刺痒得她都快笑出声了,她的手脚就软塌塌地垂了下来……张桂兰抚摸着男人肩膀上的“血蘑菇”,叹了一口气。但她还不忘矫情,白了高科举一眼:“哼,要是让儿子跑回来撞见,你就不嘚瑟了。看你那张老脸往哪搁!”
“哪那么容易让儿子撞见。”高科举浑身轻松,愉快地耸了下肩膀。
张桂兰脸上挂着笑意去外屋烧火做饭。中午的贴饼子个个都有嘎巴,黄豆芽土豆条汤,也用味精调了味,喝一口,鲜亮无比。她还给男人蒸了一碗嫩得颤巍巍的鸡蛋糕。
“快吃,一会儿儿子放学了,他要是看见,你还能捞着?”
“给守权吃吧,我不爱吃鸡蛋糕。这东西不扛饿,还是贴饼子顶饿。”
高科举一语中的,不但牛马用不上了,没过几年,就连他们费尽心思研究出来的槽道,也从森工人的眼前消失了。
山河林业局开始建设森林铁路,那个场面让所有人都欢呼雀跃。工人们争先恐后地奔到现场。山河林业局采取的是“拉开战线,分段作业,先扒草皮,再挖冻土”的办法。这个办法解决了当地气候寒冷所造成的工程进度缓慢的现实问题。当喷烟吐雾的小火车奔跑在十几条数千公里的森林铁路上,伴着车轮与铁轨的碰撞声,还有汽笛声,把一车车木材运出大山时,高科举像个孩子似的哭了。
这对森工人来说,就是震天动地的喜事。
姜占林请高科举和杨石山到小酒馆喝烧酒。他说:“今晚,我请你俩吃点儿好的。你俩尽管敞开肚皮吃肉,敞开肚皮喝烧酒。”他点了熘肝尖、青椒炒干豆腐、酱炖河鱼、猪头肉、酱猪爪、炒豆芽。吃得满嘴流油的三个人,都喝高了。
半夜,他们勾肩搭背地走在龙镇的路上,笑着,唱着,喊着。
张桂兰生完高守权后,宛若中了邪,再也不怀孕了。
冬天,高科举一上山,她就像丢了魂似的打不起精神。苗圃的人就逗她,说:“高师傅一走,你就没精打采,是不是身边没人,晚上睡不好?”张桂兰撇了一下嘴:“想他?真是闲得慌。我是想那匹马了。”
“你这话谁都不信。你到底是想你喂的那匹马,还是想喂你的那匹马?”说话的人突然想起什么,一语双关地说,“你家那匹老马,也早就不中用了。哈哈……”
张桂兰翻个白眼儿,骂了一句:“邪门,滚一边去。”
在人们的笑声中,张桂兰悻悻地回家了。其实,张桂兰一看到别的女人大肚子,或者听说谁家生了孩子,就眼红。她听人说,冬天女人爱怀孕。可是冬天刚来,男人就进山了,在山里一待就是一大冬天。她咋怀孕?她没少跟高科举抱怨:“你看尤大勺老婆,不断流地生。还有姜占林老婆,人瘦得像根刺,可人家都生了三个了,听说又怀孕了。我看,她是要生出一窝来。眼看认识的女人,今年生一个,明年又怀一个。可我就像歇伏的母鸡,生下一个孩子,就不开张了……”高科举就笑,让她别着急,说生孩子这事儿可遇不可求。
无论高科举怎么劝,她都不开心。都是女人,凭啥自个儿就生一个儿子?张桂兰趁高科举不在家,拎着半篮子鸡蛋,去找龙镇的黄半仙。据说黄半仙的师傅是鄂伦春的萨满师。一看张桂兰进来,黄半仙就抿嘴笑了,说她这辈子,命里注定没女儿,顶多还能再生个儿子。张桂兰疑惑地问:“我咋就不能再生两个女儿?”黄半仙神秘地一笑,说她能再生个儿子,还是她家男人早早地放下猎枪的缘故,否则,这个儿子都不能来。黄半仙还告诉她,高家之所以人丁不兴旺,是因为他们家祖上有人打猎,伤害过一个得道的蛇仙。张桂兰不服气,说高家祖上还治病救人呢。黄半仙撇嘴,说高家本来是到世间把人从疾苦中解救出来的郎中,没承想半道误入歧途。要不是早早收手,说不定还出啥大事儿呢……从黄半仙家出来,张桂兰闷闷不乐。
从镇子东头走到镇子北头的家,她就想通了。命里没有女儿就没有吧,能再生一个儿子也行。可这个儿子连影儿都没有……张桂兰忧伤地掉下眼泪。
高科举从山上下来,张桂兰又无端地和他怄气。这次,没了马做引子。森林铁路通车后,山上再也不需要牛马拉套子了。牲畜的作用,就是上山时帮忙驮粮食和锅碗瓢盆。再说那匹马,她养的那匹老马,老得已经派不上用场。要不是她舍不得,高科举早就把它杀了吃肉了。去年冬天,老马死了。高科举不在家,她只得找人,亲眼看着他们帮她把老马埋了。没了老马做引子,但她的气,随便一个由头都能爆发。
“看你那个脑袋,都不如鸟窝利索。”她气哼哼地瞪了高科举一眼。
张桂兰怄气,让高科举十分不解。他不想和她发生口角,他知道,家务活儿不轻松,女人也累。看她低头蹲在灶台前烧火,他没话找话,她装
作没听见。高科举的气就来了,像抓小鸡似的把她拎起来,并掐着她的胳膊,不让她动弹:“谁家的老娘儿们整天怄气?一看见我,气就来了,这还怎么生儿子?”
张桂兰扭动着身子,用脚踢他。高科举怕自己不知轻重,把她的胳膊、腿扭伤,好言好语地和她商量:“你说,我走,你生气,我回来,你的气咋还没生完?你的肚子除了装了气,还是装着气。谁家的日子,老在气里过?”先前,张桂兰用脑袋顶男人。高科举急了,像一匹愤怒的马,更像一炉膛燃烧的火,把张桂兰按倒在锅台上。开始,她还连蹬带踹。几下子,高科举就把她的身子点燃了,她就乖顺得像一只猫。
“不和你动横的,你是真不老实。怄气,你接着怄吧。”
看着走进里屋的男人,张桂兰“扑哧”笑了:“谁和你怄气了,我就是看你对我有没有耐心。”
高守利,就是高科举这次愤怒的产物。
说起来,张桂兰也是一个不让须眉的主儿。
伐木工从山上下来,就参加山下的生产会战。高科举到楞场会战,四五天没回家。张桂兰越想越不放心,就带着高守利到贮木场找他。此时的高守利,刚会走路。张桂兰刚到贮木场的院里,就看见高科举仰着脑袋望天。一群排成人字形的大雁,正从他们头上飞过去,她想男人不会闲着没事儿看大雁吧。果然,是搅盘机不走道了,钢丝绳上悬着一根一抱多粗的原木,上不去也卸不下来。试了几次,绞盘的钢丝绳都一动不动。他说一定是上头的滑轮出了问题,人得爬上去,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儿。助手咧着嘴,高科举知道他恐高。站在高科举身后的张桂兰,把儿子放到地上,对高科举说:“你看孩子,我上去。你们在下面配合我。”说着就往架杆上爬。
高科举被女人惊呆了,他像是一只听到炸雷的鸭子。
架杆六七米高,张桂兰爬到中间,冷汗就冒了出来。爬到顶上,她哆嗦了半天,试了几次才敢睁开眼睛。她惊恐地看着地上的男人,高科举冲
她摆手:“稳住,别害怕,别往下看。检查一下滑轮。”果然是不安分的钢丝绳脱槽了。她颤巍巍地伸出手,想把钢丝绳复位,扯了两下,钢丝绳纹丝不动。
“你稳住啊,先等一下。”高科举摇着手喊。
由于吊在半空中的原木比较高,矮个子男人即使伸出双臂,也使不上劲。高科举怕高守利乱跑,抱着儿子跑去叫人。十几个高个子壮汉,硬是把坠着的原木抬起一点高度……张桂兰爬下来,叫了一声“我的妈呀——”就一屁股跌坐到地上。高科举一只手把她扯起来,他左手抱着儿子,右手抱着女人。
“走,回家包饺子吃。”
林工们在他们身后起哄。后来,高科举在架杆上滑轮两侧做了挡板,没有缝隙。直径十八点五毫米的钢丝绳,就安分得再也没出轨。
(未完待续)
来 源:龙江森工
责 编:卢秋影速牛配资
发布于:北京市贵丰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